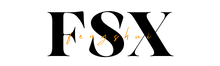2018年7月共有10天入學吉日,是5、10、11、12、14、18、22、23、24、26號。
2018年8月共有13天入學吉日,是3、4、5、8、12、16、17、18、20、24、28、29、30號。
關注我專欄朋友們可能知道,最近我籌劃成立了一個學校叫做 Q School ,找了 10 名各個領域領袖和新秀,給 30 名學生做教育。
現在 Q School 是個原型,但它是有個終極目標:我們想讓它變成一所大學,一所如果我們回到學生時代,自己會願意去讀學校。
Q School 會誕生原因直接:因為目前大學讓人滿意。
「讓人滿意」可能了。
事實上,我接觸過學生中,多半自己受教育失望。
其等待體制內改革(現在看來,可能發生),我們不如自己造個自己想要學校。
社會變遷加速使得「市場」和「教育」之間,出現了鴻溝。
吧,廢話不多説,我們進入正題,來聊聊現在大學教育,出了什麼問題:這是一個普遍問題。
大學教育,乃至於之前高中、國中、國小教育,所教授「知識」,是過時、沒有實用價值。
我説哲學、社會學、文學這樣人文學科,拿應該要有實用價值工程學科,學校教授東西跟上時代。
拿我自己例子,我大學讀是台大化工系,2007 年入學。
繫上教我們紙筆計算一個蒸餾塔高度──這種 15 年前有人寫出電腦程式解決問題,我們花時間死記背。
教授們教學內容,很多是他們 20 年前美國念書時學,原封不動拿來台灣教。
殊不知,20 年來風雲變化,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了。
,「教育跟不上市場需求」這個問題古今有、中外皆然,不是什麼台灣特有問題。
原因是,教育體系是一個「延時回饋」系統:市場端產生需求,倒逼大學輸出相應人才,而大學往前倒逼高中、初中、小學。
過去數千年來,教育是這樣子,有個幾年到十幾年延遲,問題。
然而,人類社會前所未有演化,知識增量爆漲,延遲變得不可忍受了。
打個形象化比方。
你一個中世紀出生人丟到一百年前去,他會覺得世界有什麼;但要是你今天穿越回一百年前,能感受這世紀以來翻天覆地變化。
人類社會變化速度加快!我們想像後世界會長成什麼樣子。
而今天我們要是教學生 10 年前知識,跟不上時代了。
每個人會抱怨,小學到高中這 12 年教育,沒學到什麼有用東西。
是,台灣教育重點是培育製造業技術性人才,但如今體製造業衰退,全球產業轉向創新主導知識經濟,讓台灣教育和全球市場鴻溝。
是,於大學教授來説,他們並沒有動機去主動彌補這個鴻溝。
原因是因為市場反饋太間接,影響到教授教學內容。
而作為消費者學生,面教授是弱勢一方。
如今「高等教育」頗像是監獄裡飯,做你吃什麼你得吃什麼。
吃你無反抗,只能夠忍受。
面稱職或者過時教授,我們現在唯一能夠做他們退休。
這放在 50 年前還不是什麼問題,社會發展節奏現在。
然而到了今天,我們哪裡有這種閑情逸緻呢?包容一個過時稱職教授,毀了一百個學生未來。
什麼,教育者需要接受市場機制嚴格檢驗呢?現在大學,是兩種機構混合體:是「研究機構」,另是「教育機構」。
如今一名大學教授,是一名研究員,才是一名教師,而前者後者。
大學教授升職、加薪否,是他發了幾篇學術論文、賺了多少期刊點數相關,他是不是一個「老師」無關。
我們體制上,歧視認真教學教授。
我自己遇到過很多名這樣教授:上課翻開課本開始對著黑板抄書念課本,台下學生一個眼神交會沒有,學生問問題敷衍了事,下課鈴一打急著衝回去做實驗了。
站他們角度想,這種行為並無可厚非,是他們無心教育。
而是因為人行是機製造就產物──他們多花一個時認真教書,一個時寫論文拼升等。
延伸閱讀…
如果我是一名教授,我會想要賺錢養家、升職加薪、繳房貸車貸啊!出於角度,我會怠慢教書這件吃力討活。
我台大確遇到過幾位教授,認真備課教課,投注大量心力啟發學生,讓我受用。
我到今天感激他們,因為我知道他們作為一名老師,這事是犧牲自己利益。
這些教授們情懷讓人尊敬。
但是,我們體制怎麼讓實人吃虧呢?換另外一個角度講,作為一個「研究機構」,大學功用剩多少,值得懷疑。
工業革命後幾十年,大型企業多半是國家扶持。
大學是作為國家級研發部門,國家做創新研究。
當時,大學作為研究機構是一個順理成章事情。
然而,到了 2018 年,這世界上絕大部分創新是民營企業創造,這些民營企業有自己研發部門,許多領域知識積累超過了大學。
這是什麼,如今大學研究和產業脱節,砸了一推研發經費搔不到處。
總而言,當代大學作為「研究機構」和「教育機構」混合體。
但獎勵機制上藐視「教育」,這導致教授們缺乏動機認真教書,這是一個痛點。
要講大學教育痛點,提大學入學考試了。
大學考試這到門檻,是每個年人 6 歲到 18 歲夢魘。
我們花了 12 年人生辛辛苦苦征服「魔王」,本質上是一個東西。
每個人會抱怨,小學到高中這 12 年教育,沒學到什麼有用東西。
延伸閱讀…
只是在死記背一些過時無用玩意,用以應付大學入學考試。
會這麼想,是因為你沒有看透大學入學考試,及其之前 12 年基礎教育「本質」:我們所謂 12 年基礎教育本質,不是「教育」,而是「篩選」。
大學考試制度,中國古代「科舉制度」一脈相承。
科舉制度目的,寒門子弟一條晉身階。
於統治者來説,科舉可以吸納沒背景人才,官僚系統換血,避免權力旁落;可以底層一點希望,維護統治。
科舉制度和如今大學入學考試,考是些沒有用處玩意。
什麼四書五經、論語孟子。
這官需要技能(例如帶兵打仗、賑災治水、收税判案)一點關係有。
考四書五經處是什麼?這玩意雖然死板,但教材那幾本,大家買得起。
一個鄉村窮學生一個京城富學生起跑線是差不多,要考得卯起來死記背。
考試死板可以讓篩選人羣範圍盡量擴。
學生讀了什麼,這並。
科舉制度像是一門運動比賽,要記憶力、肯吃苦、耐力年人篩選出來。
至於出社會後需要技能,開始工作後幹邊學好了。
仔細想想,這是不是我們當前大學考試相似?台灣大多數學校是公立,教育資源接受政府調配,負擔著政府部門篩選人才重任。
而過去確有大學生,畢業後很多去了政府部門或是公營企業。
而到了 20 年科技爆發,私人企業崛起後,需要一個可用篩選機制,羣人中「腦子」人篩選出來。
這是什麼,你説台灣過去教育體系「失敗」或「很」可以。
從「教育」角度來説,這個體系是失敗。
台灣學生普遍缺乏創造力和獨立思考能力,與世界趨勢落後了一大截,養出一羣「高分低能」書獃子。
從「篩選」角度來説,這個體系過去是。
它低成本方式,篩選出「人羣中有潛力」年人,投入政府部門發展方興未艾私人企業。
這個篩選機制顧及了社會底層,讓人家孩子可以苦讀出頭,改換門庭。